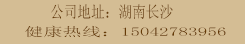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铅中毒事件 > 急性铅中毒中医 > 苏轼前赤壁赋的ldquo跨体r
当前位置: 铅中毒事件 > 急性铅中毒中医 > 苏轼前赤壁赋的ldquo跨体r

![]() 当前位置: 铅中毒事件 > 急性铅中毒中医 > 苏轼前赤壁赋的ldquo跨体r
当前位置: 铅中毒事件 > 急性铅中毒中医 > 苏轼前赤壁赋的ldquo跨体r
点击上方蓝字 噫,倚兰桨兮,我今恍惚遗身世。渔樵甘放浪,蜉蝣然、寄天地。叹富贵何时,功名浪语,人生寓乐虽情尔。知逝者如斯,盈虚如彼,则知变者如是。且物生宇宙各有司,非已有纤毫莫得之。委吾心、耳目所寄。用之而不竭,取则不吾禁,自色自声,本非有意。望东来孤鹤缟其衣,快乘之、从此仙矣。[21]
庆元五年己未()十二月十六日,作者自丹阳经江南运河至吴江,过垂虹桥,作此词。
序中可知,周生原先对于创作隐括词并不理解,故持否定态度,他认为刘学箕完全有能力自己创作,何必“缀辑古人之词章”,而刘学箕则认为隐括词是“寓意于言之所乐”,“取其言之足以寄吾意者,而为之歌,知所以自乐耳”,是以创作隐括词作为一种精神寄托,与古人心灵对话,这种乐趣是自己创作所不能代替的。
此词隐括前后《赤壁赋》,将两赋融为一体,有自身体验、个人情调,较原作有变化,如“听洞箫、绵延不绝如缕,余音袅袅游丝曳”,去除了原作“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”的悲情,而叹“富贵”、“功名”,则境界不如东坡高。
林正大《括酹江月》云:
泛舟赤壁,正风徐波静,举尊属客。渺渺予怀天一望,万顷凭虚独立。桂桨空明,洞箫声彻,怨慕还凄恻。星稀月淡,江山依旧陈迹。因念酾酒临江,赋诗横槊,好在今安适。谩寄蜉蝣天地尔,瞬目盈虚消息。江上清风,山间明月,与子欢无极。翻然一笑,不知东方既白。[22]
词用入声韵九屑、十一陌、十二锡、十三职、十四缉,急促迫切,阻滞不畅,表达悲怆的历史沧桑感,感情潜气内转,内敛婉曲表达。林正大为宋代最“专业”的隐括词人,创作的隐括词数量最多。其《风雅遗音》自序云:“余暇日阅古诗文,撷其华粹,律以乐府,时得一二,裒而录之,冠以本文,目曰《风雅遗音》,是作也,婉而成章,乐而不淫,视世俗之乐,固有闲矣。”[23]
宋末元初刘将孙十分推崇苏轼前后《赤壁赋》,《风月吟所记》云:“‘唯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取之无尽,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’者,东坡之淋漓放浪,固如在目中也。此风此月,千古常新。吾吟吾所,绝尘奔轶。二仙(按:另一仙指李白)者精意浮动,吟风弄月,如将见之。”[24]
又将其隐括成词,《沁园春》词序云:“近见旧词,有隐括前后《赤壁赋》者,殊不佳。长日无所用心,漫填《沁园春》二阕,不能如公《哨遍》之变化,又局于韵字,不能效公用陶诗之精整。姑就本语,捃拾排比,粗以自遣云。”其一隐括《前赤壁赋》,词云:
壬戌之秋,七月既望,苏子泛舟。正赤壁风清,举杯属客,东山月上,遗世乘流。桂棹叩舷,洞箫倚和,何事呜呜怨泣幽。悄危坐,抚苍苍东望,渺渺荆州。客云天地蜉蝣。记千里,舳舻旗帜浮。叹孟德周郎,英雄安在,武昌夏口,山水相缪。客亦知夫,盈虚如彼,山月江风有尽不。喜更酌,任东方既白,与子遨游。[25]
作者不满刘学箕《松江哨遍》,认为隐括得不好,称赏苏轼《哨遍》隐括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富于“变化”而又“精整”,自谦己作不如苏词,只是“自遣”而已。
他追求的是不改变原作意旨、格调,而只是变为音调谐和的韵文。沈祥龙《论词随笔》云:“坡公《赤壁赋》云:‘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,余音嫋嫋,不绝如缕。’词之音节意旨,能合乎此,庶可吹洞箫以和之。”[26]强调词的音乐性。
三
隐括词是将其他文体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,一般是对文学经典的改写或缩写。
苏轼为开宋代隐括词风气之先者,如《哨遍》隐括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、《水调歌头》隐括韩愈的《听颖师弹琴》、《定风波》隐括杜牧的《九日齐山登高》等,黄庭坚也创作过隐括词,如《瑞鹤仙》隐括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。
隐括词不是原创,宋人喜作隐括词,是出自对文学名家及其经典作品的倾倒,隐括过程即是欣赏赞叹过程,与原作者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,借他们之酒杯,浇自己之块垒,以寄托情感,因前人先获我心,心有戚戚焉,故不必新创作。
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人当时所推崇的古今文学经典。
隐括词是一种文体实验,是对文体的改编转化,丰富了词的表现力,拓展了艺术表现领域,也是对经典的重新演绎,赋予音乐性,以供歌唱,更便于传播接受。
一般大致保持原作主旨、意境和格调,较忠实于原作,最大限度地采用原作词语,有些词人如刘学箕则有自己的语言和情调。
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批评说:“东坡隐括《归去来兮》、山谷隐括《醉翁亭记》,皆堕恶趣。天下事为名人所坏者,正自不少。”[27]过分贬低隐括词的价值。
散曲中亦有对《前赤壁赋》的隐括改编,元初孙季昌[仙吕·点绛唇]《集赤壁赋》将《前赤壁赋》隐括为散曲套数,套数由不同的曲牌组成,如同交响乐:
万里长江,半空烟浪,惊涛响。东去茫茫,远水天一样。
[混江龙]壬戌秋七月既望,泛舟属客乐何方?过黄泥之坂,游赤壁之傍。银汉无声秋气爽,水波不动晚风凉。诵明月之句,歌窈窕之章。少焉间月出东山上,紫微贯斗,白露横江。
[油葫芦]四顾山光接水光,天一方,山川相缪郁苍苍,浪淘尽风流千古人凋丧。天连接崔嵬,一带山雄壮。西望见夏口,东望见武昌。我则见沿江杀气三千丈,此非是曹孟德困周郎?
[天下乐]隐隐云间见汉阳,荆襄,几战场,下江陵顺流金鼓响。旌旗一片遮,舳舻千里长,则落的渔樵每做话讲。
[那吒令]见横槊赋诗是皇家栋梁,见临江酾酒是将军虎狼,见修文偃武是朝廷纪纲。如今安在哉,做一世英雄将,空留下水国鱼邦。
[鹊踏枝]我则见水茫茫,树苍苍,大火西流,乌鹊南翔。浩浩乎不知所往,飘飘乎似觉飞扬。
[寄生草]渺苍海之一粟,哀吾生之几场。举匏樽痛饮偏惆怅,挟飞仙羽化偏舒畅,溯流光长叹偏悒怏。当年不为小乔羞,只今唯有长江浪。
[尾声]谩把洞箫吹,再把词章唱。苏子正襟坐掀髯鼓掌,洗盏重新更举觞。眼纵横醉倚篷窗,怕疏狂错乱了宫商。肴核盘空夜未央,酒入在醉乡。枕藉乎舟上,不觉的朗然红日出东方。[28]
散曲用下平声韵七阳、上声韵二十二养、去声韵二十三漾,音调铿锵,悦耳动听,但去除原作中的下平声先韵,上平声微韵、东韵,入声月韵、陌韵,声情显得单调,未能充分表达原作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。表现赤壁之战真实历史更直接,也有个人对历史的新解读。
《前赤壁赋》表现内心矛盾,但终究关怀世事,热爱生活,人生态度旷达超脱,孙季昌改编后的《集赤壁赋》则情调低沉,思想消极,两者语言虽大致相同,而表现的人生态度却差异较大,这正是元代时代精神在作者身上的折射。《集赤壁赋》将不可歌的赋改编为可歌的散曲,变成符合时代欣赏口味的歌曲,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,也扩大了原作在元代的影响。
清徐基也有散曲套数《隐括赤壁赋》云:
[南吕·宜春令]岁壬戌,时孟秋,喜风光,飘然放舟。携樽呼友,清风一棹吹江口。共歌来窈窕音缪,正相与闲行未久。少焉,月光托起在东山后。
[太师引]望寥天,横星斗。苇苍茫,是东岸西畴。羡万顷波光相缪。安放我泛月凌秋。冯虚去登仙,饮酒我乐甚,唯将舷叩歌,可有兰舟桂舟?空怀望美人今夜出来不……[29]
这是隐括曲,较原作通俗,同时是散曲的雅化。
四
戏曲、小说还将前后《赤壁赋》搬演为长篇故事,据《古本戏曲剧目提要》、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,现存19种苏轼题材古典戏曲中,以《赤壁赋》为本事或涉及《赤壁赋》的戏曲就有10种,占总数一半以上。
如元代费唐臣的杂剧《贬黄州》(正名《苏子瞻风雪贬黄州》),无名氏的杂剧《赤壁赋》(正名《苏子瞻醉写〈赤壁赋〉》);明许潮的杂剧《赤壁游》(正名《苏子瞻泛月游赤壁》),沈采的传奇《四节记?苏子瞻赤壁游》(残存),黄澜的传奇《赤壁记》(残存)等;清代姜鸿儒的传奇《赤壁记》,车江英的杂剧《游赤壁》等。
当然,戏曲有虚构加工,有些方面与历史真相相距较远。戏曲这一艺术载体丰富了《前赤壁赋》的内涵,重塑了苏轼形象,体现出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,为《前赤壁赋》的“经典化”做出很大贡献。[30]现当代与《前赤壁赋》相关的戏曲有熊文祥主创的黄梅戏《东坡》、杨锐改编的越剧《新狮吼记》、林依豹的闽剧《苏东坡游赤壁》、汉剧《苏东坡游赤壁》等,这些剧目对东坡赤壁有不同的理解,每一部戏曲皆可与《前赤壁赋》比较研究。
当然,这些还只是跨文学文体接受,只是在文学范围内接受,书法、绘画、音乐等,也对《前赤壁赋》的传播与接受做出很大贡献。
苏轼自己亲自书写《前赤壁赋》,元丰六年(),苏轼《与钦之》云:“轼去岁作此赋,未尝轻出以示人,见者盖一二人而已。钦之有使至,求近文,遂亲书以寄。多难畏事,钦之爱我,必深藏之不出也。又有《后赤壁赋》,笔倦未能写,当俟后信。轼白。”[31]
历代不少书法家以临摹或重书《前赤壁赋》为乐事。历代画家如元代赵孟頫,明代唐寅、仇英等,皆画有东坡游赤壁图。将《前赤壁赋》隐括成词,被之声歌,词其实就是音乐。这些都是超越文学本身对《前赤壁赋》的接受。《前赤壁赋》传播载体多样,传播范围广泛深远,直入人心,是其他文学经典难以比拟的。
《前赤壁赋》高妙精绝,成为后世文学、艺术广为表现的内容,涌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文和艺术精品,明魏学洢所作《核舟记》生动描述了一件用桃核雕刻成的苏轼游赤壁的微雕工艺品:
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,能以径寸之木,为宫室、器皿、人物,以至鸟兽、木石,罔不因势象形,各具情态。尝贻余核舟一,盖大苏泛赤壁云。
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,高可二黍许,中轩敞者为舱,篛篷覆之。旁开小窗,左右各四,共八扇。启窗而观,雕栏相望焉。闭之,则右刻“山高月小,水落石出”,左刻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,石青糁之。
船头坐三人,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,佛印居右,鲁直居左。苏、黄共阅一手卷,东坡右手执卷端,左手抚鲁直背,鲁直左手执卷末,右手指卷,如有所语,东坡现右足,鲁直现左足,各微侧,其两膝相比者,各隐卷底衣褶中。佛印绝类弥勒,袒胸露乳,矫首昂视,神情与苏、黄不属,卧右膝,诎右臂支船,而竖其左膝,左臂挂念珠倚之,珠可历历数也。
舟尾横卧一楫,楫左右舟子各一人,居右者椎髻仰面,左手倚一衡木,右手攀右趾,若啸呼状,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,左手抚炉,炉上有壶,其人视端容寂,若听茶声然。
其船背稍夷,则题名其上,文曰:“天启壬戌秋日,虞山王毅叔远甫刻”,细若蚊足,钩画了了,其色墨,又用篆章一文曰“初平山人”,其色丹。
通计一舟,为人五;为窗八;为篛篷,为楫,为炉,为壶,为手卷,为念珠各一;对联、题名并篆文,为字共三十有四。而计其长曾不盈寸,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。嘻,技亦灵怪矣哉。[32]
作者按空间顺序刻画,从两头到中间,从正面到背面,直观展现了《前赤壁赋》所营造的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的优美意境,刻画人物生动传神,语言平实、洗练。有关《前赤壁赋》的工艺美术还有如同治游赤壁赋壶、《前赤壁赋》银盘等。
综上所述,历代诗、词、散曲、戏剧、书、画、工艺美术等,皆有对《前赤壁赋》的模仿学习,也是《前赤壁赋》的“再创作”,因此,我们应开阔视野,不能仅仅局限于就赋论赋、就文学论文学。
《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》简介
本书是作者欧明俊二十年来研治宋代文学四大家即欧阳修、苏轼、陆游、辛弃疾部分成果的结集,论及四大家家世、生平、学术思想,诗、赋、散文、词各文体,既有文本解读、经典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分析,又有学术思想评价、研究史梳理。注重突破“专业”局限,会通研究,在学术大视野中评价四大家,尤重学术“命名”及研究之“反思”。努力还原被“肢解”的文学大家“全体”形象,还原文学史“原生态”。附录《问学小言》《微言录》,既见学识,又见性情,颇值一读。《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》由人民出版社年10月版。注释:
[1]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二十八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[2]胡助《纯白斋类稿》卷一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[3]徐基《十峰集》卷一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卷,第页,齐鲁书社年版。
[4]徐基《十峰集》卷一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卷,第页,齐鲁书社年版。
[5]徐基《十峰集》卷一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卷,第页,齐鲁书社年版。
[6]永瑢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下册,第页,中华书局年影印本。
[7]强行父《唐子西文录》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[8]王文濡《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》卷七十一引,中华书局年版。
[9]贺培新《文编》卷下,天津民国日报社年版。
[10]戴表元《郯源戴先生文集》附《郯源佚诗》卷六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[11]陆文圭《墙东类稿》卷十九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[12]田雯《古欢堂集》卷十三,清康熙刻本。
[13]文天祥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十四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[14]王恽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三十三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[15]胡助《纯白斋类稿》卷十一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[16]徐基《十峰集》卷二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卷,第、页,齐鲁书社年版。
[17]徐基《十峰集》卷二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卷,第页,齐鲁书社年版。
[18]徐基《十峰集》卷四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卷,第页,齐鲁书社年版。
[19]唐圭璋《全宋词》(三),第—页,中华书局年版。
[20]万树《词律》,第15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。
[21]唐圭璋《全宋词》(四),第—页,中华书局年版。
[22]唐圭璋《全宋词》(四),第页,中华书局年版。
[23]林正大《风雅遗音》卷首,清徐釚钞本。
[24]刘将孙《养吾斋集》卷二十二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[25]唐圭璋《全宋词》(五),第页,中华书局年版。
[26]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第五册,第页,中华书局年版。
[27]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第一册,第页,中华书局年版。
[28]郭勋辑《雍熙乐府》卷五,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。
[29]徐基《十峰集》卷二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卷,第页,齐鲁书社年版。
[30]参见赵义山、田欣欣《论元曲家笔下的苏轼形象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年第2期;衣若芬《剧作家下的东坡赤壁之游》,《中国苏轼研究》第二辑,第页,学苑出版社年版;郭茜《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东坡赤壁故事》,《社会科学辑刊》年第1期;张媛《元明戏曲小说中的苏轼形象》,《安庆师范学院学报》年第2期;邵敏《东坡赤壁的戏曲传播》,《四川戏剧》年第6期。
[31]张志烈、马德富、周裕锴主编《苏轼全集校注》第二十册《苏轼佚文汇编》卷二,第页,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版。
[32]张潮辑《虞初新志》卷十,第—页,文学古籍刊行社年版。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qianzhongdushijian.com/jdzy/4475.html